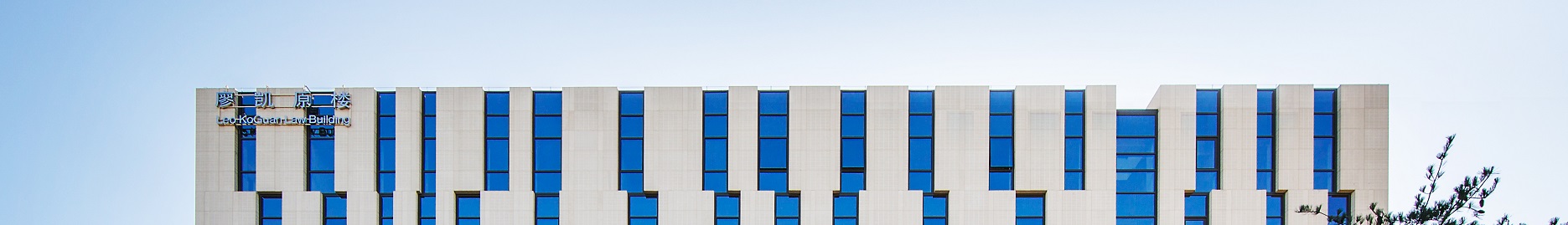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一)淡淡的回忆——悼念张铭新老师
我想,我不希望惨惨淡淡愁云满面地回忆张老师的故事,因为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自信而乐观的人生态度,于是直到今天,等张老师逝世的悲痛已经被时间所淡漠之后,我才愿意写下这些点点滴滴。
因为并不带研究生,所教授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对于整个法学学科来说又相对较为冷门的缘故,我对张铭新老师的学术造诣其实了解甚少。其实可以理解,给一帮刚刚迈入法学门槛的本科生上大课,讲的太过深奥则一无机会二无必要。但对于一门原本无比枯燥的法制史课,张老师通过他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却给我留下了非常多记忆深刻的片段。
张老师最常用的开场白,是他那能让全场短时间内肃静下来的独特的微笑。一副画面留在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心中:在上课前全场一百多号人闹哄哄地瞎聊的时候,踱进来一位头发花白但身板挺直的老教授,施施然踏上讲台,放下讲义立定,双手撑讲台身往前倾,随即一个神秘的微笑凝固在面庞后纹丝不动,不发一言。大体不过五秒,全场皆静,此时张老师便说:“大家~~都~~~说够了吗?说够了~~~~咱们~~~~~就开始吧……”
三年后,在我们年级的毕业大戏中,我们同学对本科四年所受教过的印象深刻的老师进行了cosplay,cos的老师的台词均是出自于大家的回忆和当年的课堂笔记,而作为很生僻的法制史课程的授课老师张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扮演者是我们一位在学校艺术团待过的现在已经是一名法官的女同学,虽然性别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她最具备张老师那种独特的文人气质。而一些完全出自张老师课堂笔记的台词,我们到现在还有所记忆,例如谈到古代的刑罚,张老师说“为此,我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博物馆,也就是明清历史档案博物馆,啊,也是就故宫啊,查了一些资料”,此言一出大家都大笑,注意力一下就集中起来了,又提到商朝的五种刑罚,墨劓刖宫大辟,张老师说“墨刑啊,就是往犯人脸上刺~~字,不同的罪名~~~在不同的地方~~~刺不同的字,当时~~很多人脸上啊~~~都刺满了字。再说那个劓吧,就是割鼻子,割下来的鼻子啊~~~都是一车一车的。还有那个刖,就是断足,当时割下来的脚啊~~都堆成山,据说因为这个刑罚啊,鞋都卖不出去,因为大街上尽是没脚的啊~~……”
而张老师更多为我们所传诵的,还是他与教我们婚姻法的陶毅老师之间的感情。我们是先上的法制史课,后一个学期才开始上婚姻法课,记得婚姻法第一堂课时,张老师站在门外静静地听着,我们同学都很纳闷张老师为什么过来,课间休息时,张老师走了进来,略有腼腆地跟大家说“陶老师是我夫人,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尽量不要给陶老师添麻烦”,当时同样是全年级哗然,根本没有想到平时看起来都非常严肃和学术的老师们也有这么生活化的一面。然后大家八卦出他们原来是大学同学,相恋相知走到一起,相濡以沫到老。而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我们不停听到说谁谁谁今天又碰到张老师等陶老师下班后骑车带她回家,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师跟年轻小恋人一样骑着车慢慢归家的场景,觉得简直无比的浪漫。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某次婚姻法课上谈到女性家庭地位的事情时,陶老师略带小孩气式的骄傲地说“谁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我在家里就不做”,当时大家顿时八卦之心猛涨,底下纷纷议论没听说陶老师跟张老师家里有保姆啊,他们孩子也不住一起啊,看来一定是张老师做家务了哇哈哈哈。而从陶老师本人的脾性来看,我们真的相信,张老师在家里真的是把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宠着爱着。而这,也许是婚姻法课程进行过程中最好的旁注吧。
作者:熊定中(2000级本科)
(二)纪念张铭新先生
我不是个好学生。大学四年,能做到不逃课的课程屈指可数,更难得有门课能认真听讲。
张铭新先生的《中国法制史》和《中国近代法制研究》是极特例,不但从未缺勤,还很认真做了笔记,有些课竟然还保存着录音。与法学相比,显然我对历史更感兴趣。
院里总有因先生年事已高,开设的某门课程是最后一次的传言,也就总有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享受着先生“关门弟子”的待遇。
记得毕业后一次回院里偶遇先生,又见到他标志性的微笑,顿时由衷的体会到一种幸福感。先生若想起桃李满天的学生们,离开时,也定会带着微笑吧。先生走好。
下面是2006年《中国法制史》最后一课尾声时的录音,以此纪念远去的大师:
非常高兴和你们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学期。(掌声)有位同学说张老师爱笑,虽然这个笑不一定发自内心,(笑声)但是还不惹人讨厌。有这样的话吧?我看一位同学的网上日记是这么说的。(惊叹)不惹人讨厌让我十分高兴,说明一点的就是,我这个笑,可确乎发自内心啊,哈哈哈。(掌声)
我对你们十分的喜爱——我这个年龄说喜爱可以了哈,(笑声)起码比你们的父母要大。有的学生在网上以更亲的名字相称。对你们非常喜爱,也非常关心,期望也非常大。这些都出自内心。
教了几十年学了,确实有我的学生,说千千万万夸张了啊,说是数以千计似乎可以,对吧?以前的这些同学呢,应该说绝大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有很多的人物,也非常的杰出,我深感安慰。
这些人物分布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在学术界,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像季卫东、钱明星、李仁玉、马作武,等等等等。一批现在相当有名的学者,我都教过他们。有的是本科生,有的是研究生。
还有一批人活跃在律师界。很多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现在叫合伙人,都是起码见面叫老师的,呵呵。比如我的一个本科的学生在武大教的,一个著名的跨国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同时还身兼着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惊叹)还兼着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惊叹)
学界里面还有一个最近吵的沸沸扬扬的人物,我也可以说那是我学生,虽然最近这事弄的很讨厌,就是周叶中。周叶中那事弄的有点讨厌是吧?还有一批分布在政界,包括公检法。比如公安部的法制司的法制局局长,治安局的副局长,最高法院的民行庭(注:民行庭是最高检设置的机构,疑似口误)的副庭长等等。这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我现在很有成就感呵呵。(笑声)
老师就是希望学生们成才的。所以虽然我们这门课在你们整个的知识结构里面,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希望通过学习这门课,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够很快的成才,为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你们!(掌声)
作者:郑厚哲(2005级本科)
(三)大师当如此
8月25日下午3点,张铭新教授纪念会在明理楼举行。会上,我作为先生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做了简短的发言。经过与会其他老师同学的发言,对一向低调的张铭新老师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原来先生是如此内心充满爱与责任,如此淡定从容,如此克己勤奋,如此豁达高尚的一位先生。 纪念会上,几次感动得落泪。以下为会上发言稿,以此深切缅怀敬爱的张铭新教授。
在讲话前,请允许我作为曾授业于张铭新教授的学生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哀悼。
2006年,我带着对大学的憧憬来到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师云集的法学院中,一向低调的张铭新老师也许并不能算是风云人物,然而先生的儒雅与谦和,一直让我感到由衷的敬意和亲切。作为法六年级的一分子,有幸在中国法制史的课堂上聆听先生的教导。
单纯从这门课的成绩上讲,我并不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学生,但是对这个课堂却有着很高的热情。张铭新老师讲课细致而生动,内容丰富而精彩。在上课前,年逾花甲的他总是精神矍铄地走进教室,微笑和蔼而淡定,轻轻放下讲义和教案,待上课铃响过后,开始讲课。每堂课结束,先生从不忘记讲一句“谢谢同学们”,然后在掌声中给课件做好书签,向同学们摆摆手,露出淡淡的微笑。先生的笑容是让人难忘的:烔烔有神的眼睛笑成浅浅的弧度,闪烁着慈祥的光芒;牙齿轻轻盖住嘴唇,嘴角上扬,如此和蔼与安然,让人轻松;岁月在先生脸上留下的皱纹,却也更加显出他的深沉宽厚与满腹经纶;两鬓银发虽日渐增多,却愈发衬出先生可亲可敬。
张铭新老师对待教学是认真负责的。先生上课内容很详尽,有时候会完不成预定的教学进度,到了最后一节课却还没有完成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史的教学。先生对我们说:“古代法制史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短短的一个学期让我有些意犹未尽。下个学期我再上两节课把剩下的内容讲完,同学们自愿来听。谢谢同学们。”我们在座位上静静地听着,感动于先生对法制史与法律教学事业的热爱:先生永远是一个负责任、爱学术、爱讲台、爱学生、博学儒雅、激情澎湃的大师。
讲台上的先生是有魅力的:清晰洪亮的声音,幽默优雅的谈吐,厚重渊博的学识,深沉严谨的态度,温文尔雅的风度,从容谦和的心态,都展示着一位大师的修养与气质。先生在课堂上从不点名,但出勤却很好;先生的课堂很少有无精打采睡眼惺忪的同学,几乎每个同学都积累下了厚厚的课堂笔记。而今重新拿起这叠珍贵的笔记,看着有些泛黄的纸张,看着不再那么清晰的字迹,静静地阅读那些传递着知识与思想的话语,先生当年授课时的音容笑貌仍会浮现在耳畔脑海。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恩师的逝去并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也可能是因为先生对我,对法六这个年级,乃至对整个法学院的影响是那么深刻,以至于永不消散。
作为教师,一门课程所传授的知识也许并不会在学生的生命中留下很深的印记。然而先生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因为他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教会我们如何治学与为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言传身教,以个人的魅力与感染力,让我们变得有知识也有文化,有教养也有修养,有追求也有情操,有勇气也有担当,有性情也有思想。
想起先生四年前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样子,怎么也没想到会有如此大的变故。8月6日,我在自习时突然得知先生离开的消息,顿时失语。这样一位法制史学界的大师,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这样一位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教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敬爱的张铭新老师永远是那么儒雅而谦和,大师正当如此。学生当以毕生之精力追寻先生的风格与气度,先生之恩情永记,先生之精神永生!
以此缅怀张铭新老师,祝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陈熹(2006级本科)
附:张铭新教授生平[2]
张铭新教授1942年9月生于北京,蒙古族,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
张铭新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第13中学,1964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嗣后在新疆精河、博乐等地从事司法实践工作。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主攻专业为中国法制史。1981年毕业并成为我国首批法学硕士之一。同年到武汉大学执教,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3年晋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台湾法研究等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1995年5月,张铭新教授从武汉大学调入清华大学,参与法律学系的筹备复建工作,曾担任法律学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法学院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铭新教授热爱教育、科研事业,他所讲授的每一门课程,都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著述丰硕,是我国法律史学界的知名权威。2006年10月,张铭新教授退休后,仍然非常关心法学院和学校的发展,为法学院法律史学科的发展和清华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做了很多工作。
张铭新教授曾担任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儒学与法文化研究会理事。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命题专家,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主讲教授。还在若干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等。
张铭新教授的代表著作包括专著《中国法制史纲》(独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专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与陶毅合著,东方出版社1994年7月),主编《中华小百科全书法学卷》(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6月),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与李贵连教授合著《清朝命案选》(法律出版社1982年8月),统稿《中国法制史提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等等。其他参编教材、书籍11种。
著有论文、古案例研究数篇,包括《关于秦律中的“居”——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质疑》(载《考古》1981年1月),“秦律中的经济制裁—兼谈秦的赎刑”(载《武汉大学学报(社)》1982年4月),《离婚:单一破裂主义或混合主义》(载《法学研究》2000年1月)。
2011年8月1日,张铭新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1] 张铭新老师生前没有接受过学生访问,编者收集了学子所写纪念文章,作为追忆。
[2] 见清华大学法学院主页,http://www.law.tsinghua.edu.cn/publish/law/3251/2011/20110825180220884138245/20110825180220884138245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