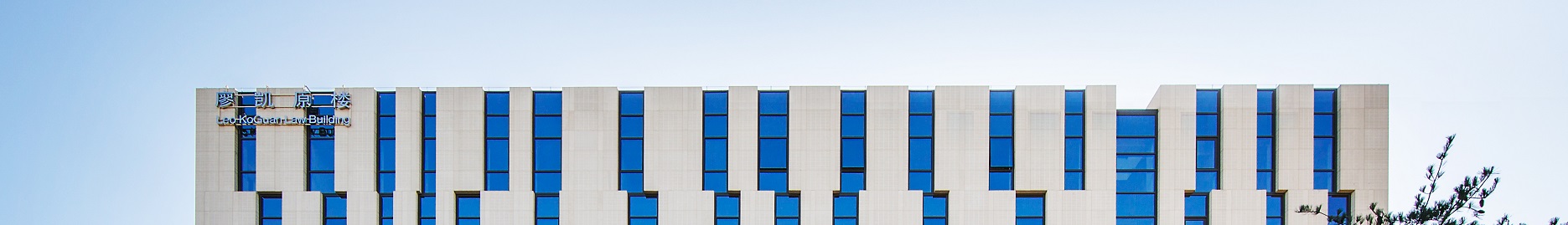车丕照,曾先后获得吉林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硕士,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曾出版《国际经济交往的政府控制》、《国际经济法原理》、《国际经济法概要》等代表性著作。
明理楼,清华大学法学院主楼。在二楼的西南角,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这间不足卧室大小的屋子,便是车丕照老师工作学习的地方。
四张不大的单人沙发紧靠墙边,两面小方桌挤在中间,其中一张堆满了书,环墙三面的高书架上放满了各类书籍,就连办公桌上横着的、竖着的也都是书。这既是老师办公、研究的场所;也是老师接待访客、与大家促膝长谈的地方。
书本,朴实,知识。这大概就是我们初访车老师的第一印象。
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走了30年
在学术界,车老师毫无疑问是我国国际经济法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然而,国经方向并不是车老师的最初选择。“选择国际经济法其实不是一个什么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车老师对记者说,“当初高考报志愿时,我选择的是中文专业,结果成绩不够,被调剂到法律专业。我们高考那年是全国第二年招法律专业,大家对这个专业都不是特别熟悉。准备硕士生考试时,本来想学刑法。有同学说,你英语还不错,可以读国际法。于是我报考了国际法。其实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学习ABCD的。读研究生之后,也不是主要读国际经济法。那是1982年,国际经济法也是刚出现的学科,所以读国际法方向主要学的是国际公法。后来到美国读书,我就问带我的老师,我可不可以学习国际经济法方向,老师说可以,我就开始研究国经了。所以,选择国经并不是我的初衷。”车老师如此揶揄起这段经历。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偶然的路,车老师一走就是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的历程中,车老师兢兢业业,不断学习,不断汲取新的知识。看到车老师办公室堆放的各式各样的书籍,不仅有国际经济法相关的书籍,还有一些其他法律类书籍,甚至是文学书籍,记者不禁问道,学国际经济法难道还要读文学书籍?“法学学科需要很多学科做支撑。通常,我们学习法学要看很多文书,这些文件从表面上看是法律文书、法律文件,但是其内容很多是非法律的东西,比如财务报表、账单、往来信函、媒体报道等等,这会涉及到很多东西,这样一来就会逼迫你去学习很多东西。学社会科学可能会比学理工科还需要更广阔的贮备,所以我觉得社会问题比自然问题更复杂一些,视角越多,判断可能越趋向于准确。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课堂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问题可能牵扯到合同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等等许多法律部门。”正如车老师所说,法学学科非常庞杂,因此,车老师注重学生逻辑思维和发散思维的训练,一个问题,一个答案,一个逻辑论证过程。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车老师总是不紧不慢地走进教室,从手提袋中缓缓拿出讲义,翻到要讲的部分。车老师不是常用PPT,即使用也要拿着讲义。每周三节课,一个课题,车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在清华法学院,你一定要去听车老师的课”,这是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何隽老师在课堂上给予车老师的评价。
优势需从细微处着手
清华大学法学院与其他学校法学院相比,有其独特的品牌优势,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清华大学优质的生源造就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品牌。谈及对法学院学生初入社会的意见和建议,车老师与记者分享了几个小故事,让记者感触颇深,“有一次我请了一个法官来做讲座。法官在讲话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水喝。后来我让同学帮忙弄一杯水给法官喝。于是同学就出去买了一瓶矿泉水。但是法官还是继续讲,并没有打开水瓶。我又让同学去找一个纸杯来,把矿泉水到在纸杯里,这样子法官就比较方便喝水了。像这个问题就是非法律问题,却是任何人走进社会都要接触的问题。像这种怎么来和同事、上司或当事人相处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但却很重要。我见过有的律师一见到当事人就要训斥,好像当事人是他的下级似的。同学步入社会之后,一定要认真地观察,去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怎么做得好。在社会上,待人接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初入职场的学生来说。至于在执业中该如何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我倒是觉得相对于非法律的问题要简单一点。对于法律问题,一定要思考问题和依据在什么地方。学法学学到最后就是一个法律关系的问题。法律关系就要找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客体、法律关系内容。比如谁是被告?是租赁还是保管亦或是买卖等等。法律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保证这样大的方向就可以了。到了律所可能一下子遇到很多很琐碎的问题,这些都是十分锻炼人的。我有个学生在香港一家律所实习。有一次我去香港讲课,和他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一个他的经历。他的上司要他查找一份资料,他查找之后如实的把资料交给老板。结果第二天他的老板拿出了他自己查找的一份资料,差别很大,老板所查找的资料明显比他要多很多。我就问,你们是不是检索工具不一样,或者检索关键词不一样。他说都不是,他说差别在于,他查了两百多页,而老板查了四百多页,就只是这样一个区别。这其实不是法律知识问题,是一个习惯和态度问题,和人的素质有关。但如果这是两个律师之间的区别,可能就涉及丢饭碗的问题了。总而言之要注重细节,从细节处努力。”
给清华多一些时间
2015年是清华法学系复系20周年,法学系恢复之初,车老师便加入了法学院的队伍。访谈中,谈及老师与清华法学院的故事,车老师感慨道:“清华法学院的老师非常勤奋,晚上十点都还有许多办公室亮着灯;在清华法学院,老师是不允许做实质性兼职的,所以老师能够专心搞学术,我想这也是清华法学院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在国内,清华法学院还没有名列三甲,但是在国际上,清华是中国国内排名第一的法学院。然而对于这个“中国国内排名第一”,车老师有自己的看法。
“国内国外对我们评价不一样,按照国际上相关规则的评比,清华大学院在全球排在前五十名之内,在中国排列第一,但是把这个排名拿给人大、北大的法学院院长看,他们会不以为然。按照国内标准来排,我们有很多差距,比如我们法学院没有国家重点学科、没有‘基地’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不看。我们需要等待,等到30年、50年之后再去观察我们的学生处于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贡献。我说的位置并不是市长、部长这样的位置,而是在社会的各个主要领域。那时候再去看清华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亦或是清华法学院对中国这么重要的转型时期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主意,有什么的贡献,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标准。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多少经费,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学院整体对这个国家乃至全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是提出了什么样的重大问题?还是设计了什么样的制度?我想多年以后会有结果。谈到制度贡献,车老师坦言,中国对国际法的贡献还十分有限。比如大陆架制度是谁提出的?是美国人提出的;两百海里的海洋权是谁提出的?是拉美人提出来的;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的制度是谁提出的?马耳他人提出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国际法律制度应该有更多的贡献。”
谈及对法学院未来发展的看法,车老师说:“按照传统的说法,清华人第一就是听话,第二就是出活,老师这样,学生也这样,都比较踏实。虽然在法律业场上我们没还不能构成一个势力,毕竟我们人少,像政法大学从79年到现在,30多年,培养了数万大学生,清华在这方面无法与之抗衡。我感觉,我们法学院同学进入金融业的比较多,将来金融业可能成为清华法学院的一个优势领域。在未来,清华法学院的发展应该学会慢一点,更扎实一些。社会也应该给清华法学院多一些时间,给清华法学院学子多一些时间。各种排名固然重要,但也不必过分看重。重要的是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看清华法学院为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这可能要等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才能够看得到。我们清华法学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或未可知。”
离开车老师的办公室,我们感慨万分,车老师身上的那份严谨,那份认真,那份执着,那份从容,都令人心生敬仰,又催人奋进。
有道是:
车水马龙流年转,
丕变鸿业微处生。
照得讲台方寸间,
老校旧院新貌呈。
师门桃李天下满,
辛劳耕作硕果丰。
苦尽甘来弘法业,
了凡此愿竟功成。
【记者手记】
说起车丕照老师,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得一丝不苟、温文尔雅,若不是这次采访,谁也不曾想过老师的学术生涯会那般富有戏剧性;又或许,正是这般处变不惊,云淡风轻,才能做到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学术。听着车老师从容地讲述着自己的人生经验、学术感悟,突然感觉和课堂上那位细致严格、不怒自威的师长又有点不太一样。当我们的采访行将结束时,车老师仍不忘关心着我们的学习情况,认真地询问对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有没有疑问,并耐心地回答了大家的困惑。“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车老师用自己最坚实、最朴素的经历与知识,让台下的每一个人如沐春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我们不断奋进!
采访撰文:陈欢、吴海、许卉(2013级法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