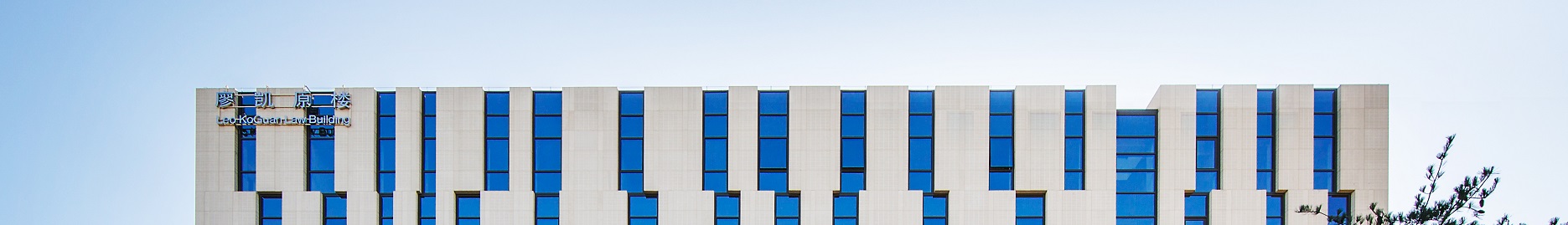程啸,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民法总则、债法、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法、损害赔偿法。现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兼职。发表《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侵权责任法》等学术专著数部。
长于临川,学于北京
我是在江西临川(现在叫抚州)出生,上的小学。临川是王安石和汤显祖的故乡。记得人民公园里就有汤显祖墓,每年秋天学校会组织到人民公园观赏菊花,回来后要写作文。人民公园里面就有一座汤显祖的墓,不过那时候并不知道汤显祖是什么人。小学毕业时,由于我父亲从军队转业,他要回自己的家乡——江西省九江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做都昌县,坐落于鄱阳湖湖畔——工作,于是我就到都昌县第一中学读书,在那儿读完了初中和高中。那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语文的老先生,他读过私塾,背过“四书五经”,小楷字写的非常的好。有一段时间,他每周辅导我一次古文,读的是古文观止中书籍中的选段,这对我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使得我到现在都非常爱好我国古典文学。
十七岁参加高考,我是文科生,当时考了九江市的文科第一名。不过,当时是估分填志愿,我当时感觉考的不好,所以什么北大、人大都不太敢报。一本报的是华政,提前录取则报了北师大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但专业不是法律就是中文。当时,对法律完全没有概念,不过我父亲是官员,认为我应当学法律。我父亲从军队专业后回到他的老家都昌县后,先是当县武装部部长,接着又担任过政法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等职务。1992年邓小平南巡,93年全国都在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说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官员,我父亲应当说还是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他觉得,既然将来要建设市场经济,就要依法办事,学法律的人就有大用处。于是,除了我自己喜欢的中文外,他要求我还报上法律。那个时候既没有网络,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可以提前考察一下,对于专业、学校,基本上父母怎么说,就怎么选。我对这些填报的学校基本没有印象。
最后,我直接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提前批录取了。这个学校非常奇怪,她是唯一的既非军事,也非师范类的提前录取学校。是共青团办的学校,校长历来由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任,毕业证上签名也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的毕业证上的校长签名就是李克强的。我毕业的那年,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那年他要到河南当省长,毕业典礼的时候还到学校与我们这届毕业生话别)。
我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现在叫做法学院了)读书的时候,法律系是第一届招生,压根没有老师。当时知道是这个情况,肯定不读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让人惊奇。正因为没有老师,结果给我们上课的全是从北大、人大、法大请来的好老师。我记得,讲刑法的是周振想教授(已经去世了)、讲宪法的是胡锦光教授、讲民法的是姚辉教授,讲行政诉讼法的是张树义教授。我们甚至开设了现在中国绝大部分法学院开不了的课,如司法精神病学(北大的孙东东教授讲授)、物证技术(人大周慧博教授)、刑事侦查(人大李学军教授)以及法医学(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的一位老太太,有几十年尸体检验经验)。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幸运,当年有机会能够同时受教于这么多的好老师。
读本科的时候,由于课程开的很多,几乎每天都要上课,往往是上午四节,下午四节,甚至晚上也要上课。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因为我觉得大学就是求知读书的地方,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或自习室看书。通常我每天会花上一到两个小时将今天学的东西复习一下,剩下的时间就是看各种法学、政治学名著,主要是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译世界名著,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律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等等。当时,看不大明白,但仍然硬着头皮看。这段读书经验对自己未来的求学研究真是奠定了思想基础。我读大学时,既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所以宿舍里同学之间的交流很多,大家没事的时候喜欢聊天,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米,聊国家、社会、个人等乱七八糟的问题。我到国外去,参加人家的聚会,发现也是这样的,喝着啤酒神侃瞎聊。现在的同学们,很多都是低头族,坐在一起吃饭都不说话,就是埋头玩手机,发微信。我觉得任何人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这是我们读大学和现在不同的地方。
结缘民法,寻治学之道
本科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民商法硕士研究生,在人大继续读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喜欢民法,而人大的民法算是全国最强的,所以就到人大去读。刚开始学习法律时,周振想老师教刑法,我觉得刑法特别有意思。后来,姚辉老师教我们民法,和民法那种自由的精神、宏大的体系和精致复杂的制度设计相比,我举得刑法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总论还凑合,一到各论,就是主体、客体、主观、客观(据说,现在刑法界已经逐渐破除了特拉伊宁的四要件说,采取了德国的三阶层论,或许刑法也没有那么无趣了)。
在人大读研究生期间,我受谢怀栻先生影响很大。一个偶然的机会,导师王利明教授让我给谢老送一个材料。之后,经常就学术上的问题请教他。那个时候我对读法律挺失望的,感觉法律的东西都很肤浅,没有什么自己的比较深入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治学方法。谢老就用了胡适先生的“为学应如金字塔”的比喻,希望我既能把基础打扎实,也能在专业上深入。既要在民法中学习民法,也要能够跳出民法之外学民法。谢老的话语就像指路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此后,我的兴趣很广,一直很关注法律之外的东西,比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这些领域的好书、新书我都会买,都会看。因为,只有这样你理解法律的视角才会多元化,才能真正深入。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学习热情是很高的。人大的课,老师讲的差就不听,如果哪个学校有什么好老师讲的课,大家会口口相传,结伴去听。比如,我就在法大听过方流芳教授的公司法和债法,在北大听过于兴中老师的法理学。在人大读书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创办了《人大法律评论》。在读博士以后,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民商法律网。
我就这样在听课、读书中度过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活。记得,那时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找工作的事情,也不像现在的同学那样有特别强烈的所谓危机感。每代人都有危机感,我们那个时候虽然研究生少,但是也同样面临找工作的压力。不过大家只是在毕业的时候,才会去为工作的事情犯愁。不会像现在一些同学,从上研究生的第一天就开始准备毕业找工作。对于这些同学来说,到清华大学法学院来,就是为了一张文凭,改换门面,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重要的是做好当下的事情,没有必要拔苗助长或杞人忧天。你现在在学校,就好好读书,快毕业了就努力找工作。未来的事情也不是你能完全决定的。
人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是很重要的。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先生的学生星野英一教授写到:“我妻先生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不是为了得到金钱和社会地位,而是为了实现理想和抱负,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这些荣誉和社会地位有可能就像一个副产品一样就来了。”当然,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过这并不是其中重要的事情。很多人没有获得这些副产品,但不能说他就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像先贤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圣人;莫扎特,死之前一直是贫困的,可是他留下来的作品确实永恒的。所以,我想很多事情要能努力地看开、看淡些,不要鼠目寸光,只盯着眼前这些东西。否则,整天蝇营狗苟,把自己卡在里面。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什么东西,你只有以其为乐,才会觉得真正有意思。当然最开始,你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可能并没感受到它的意义,就像我学法律一样,是慢慢才了解之后才喜欢上。有种长远的兴趣,在此之上的人生目标才比较有意义,准确定位自己,不要看别人怎么样。
劝学,乐与高手下棋
现在社会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大家从微信、微博上看各种来源不明的所谓“最新发现”、“必读文章”和“心灵鸡汤”。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主要时间是读书,读各种书,有些是老师推荐的,也有自己找的。读的特别多的是那些经典名著。一开始读的晕头转向,甚至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但是,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有些东西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脑海,等将来有一天你突然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像小学的时候,让小孩背“四书五经”,他不会懂其中的意义,但他背着背着就把这些文字记在了心里,等到长大后某一天遇见某件事情,脑海里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他也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像我在学生时期读过的那些经典书籍,现在却没有时间再读一遍,所以,我一直给每一届自己带的研究生强调,读书的时候不要去考虑很多功利性的东西。即便像我现在当老师,很多时候读书都是带有功利的,比如为了研究某个问题,写一篇论文而读相关的书籍。
图书馆的书我也去借,但自己也买了很多书。那个时候买书不像现在坐在屋里,通过亚马逊和京东就买来了。我买书的主要途径有两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去海淀图书城。90年代时期图书城非常火爆,书多人多,摩肩擦踵,我常常去那儿逛。有时候买,有时候也什么都不买,就看,但现在已经衰败了。还有一个是北京每年的书市,春秋两季,有时候在白石桥、动物园那块,有时候在地坛。很多出版社都会去,书也非常便宜,扎着一捆捆地卖。
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课外活动很少。也许就像古人那样,因为活动少,所以心情才静,没其他事,所以好好读书。现代社会的信息获取途径很多,微信、微博、网络导致知识的碎片化、思想的碎片化非常严重,段子文化盛行,伪知识较多。我们现在的同学多数人不愿意静下心来,去啃一些学术著作、经典著作,只读那些容易读的口水书。这就像一个人他愿意和他水平低的人下棋一样,这样你下的时间越长,你的棋艺就越臭。就像你读某些心灵鸡汤式的书,读着时很快,一目十行,但读完之后你获得了什么?读经典,就是因为很辛苦,所以你才收获很多,就像和高手下棋,老被人家修理,一直被挫败感环绕,却会有进步。我们都应该像曾国藩那样读书:“今日不通,明日再读,明日不通,后日再读,总有一天会懂。”这是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我们社会的节奏不可能再像古代那么慢,但至少我们自己的内心要慢下来。
祝福清华法学院
我是2003年博士毕业后来清华工作,03年8月份报到,9月开始上课。刚开始给本科生讲的是《物权法》,后来也讲过《民法总论》、《合同法》、《民法典专题研究》。2006年开始,在清华法学院开设并系统讲授《侵权行为法》和《侵权行为法研讨与案例分析》。算起来,在法学院也工作了12年。看着一批批的学生入校、毕业、走向社会,感觉时间过的真是太快了。
一个法学院应该有自己内在的文化气质,就像一个人那样。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学、学院更是如此。没有自己气质的法学院绝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法学院。最近二十年法学院发展迅速,但法学院气质等无形的东西还处在形成阶段。在此,我衷心祝愿清华法学院迸发勃勃生机,为学生、老师们营造一片安静、快乐的精神家园。
【记者手记】
笔者是在2014年12月对程老师进行的采访,采访共持续1个小时,听程老师讲他的求学之路,讲他如何扎进民法的世界,最直接的感受是所有让我们纠结万分的人生(职业)选择大题在老师那儿都有一个最简单、最纯粹的答案——“乐”。在此,以卡夫卡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你没有必要离开屋子。待在桌边听着就行。甚至听也不必听,等着就行。甚至等也不必等,只要保持沉默和孤独就行。大千世界会主动走来,由你揭去面具,它是非这样不可的。它会在你面前狂喜地扭摆。”
采访撰文:罗素云、马泽(2013级法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