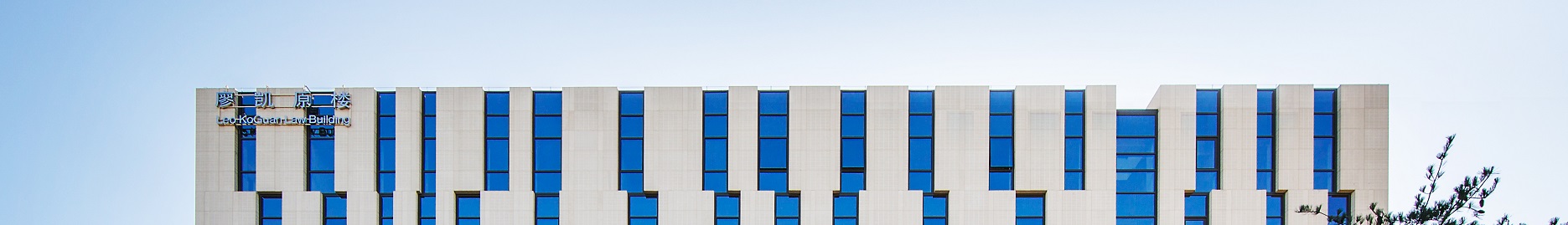崔建远,1956年5月生,河北省滦南县人,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凯原学者”,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被评为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所著《物权:规范与学说》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准物权研究》荣获司法部第二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国优秀法学科研成果二等奖;《论争中的渔业权》荣获司法部第三届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物权法》(第二版)荣获清华大学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一等奖;《土地上的权利群论纲》和《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分别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荣获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侵权责任法应当与物权法相衔接》荣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其主编的《合同法》(2000年)荣获司法部第一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作为负责人的《民法学》被批准为国家精品课程及北京市精品课程,作为负责人的民商法学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作为负责人的《债法》被评为北京市及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缘牵清华
崔建远老师于1996年8月来清华大学任教,而其工作关系则是于1997年2月才转到清华。与清华结缘,源于崔建远老师自己的选择。对于这一决定,崔老师坦言与时任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的刘海年的一番谈话有密切关联,“他说在德国,一个民法学家再著名成就再辉煌,也只不过是在注解着德国民法典。而如果我能来北京工作,比如来到清华大学工作,就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中国民法的立法工作。”与此同时,崔老师自己的一次切身经历,也给了他较大的触动与思索。“我曾参与了《合同法》的立法,当时在清华大学有一次非常重要的《合同法》讨论会议,而那次会议在《合同法》的立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只邀请了在北京工作的同仁参与,所以我就被漏掉了。如果当时我就在清华大学工作,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意识到如果来北京来清华工作,将能够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平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更好地转化为法律并产生其巨大的社会效应,甚至于能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而在与清华的接触之中,清华的诚意与妥帖也给予崔老师无比的安定与踏实之感。“我记得当时学校明确告诉我,如果来清华,学校有三居室的房子但是不能给我,是因为学校的政策是每个到清华来工作的教职员工都得从头开始,就我的情况学校将提供给我两居室,并在成为正式职工以后,参加分配排队,能分到多少就是多少。并且把我夫人安排在学校图书馆,把孩子是安排到清华附小。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告诉得很清楚。清华的安排让我心理很踏实,曾经那种因为不了解清华而忐忑的心情也在清华的诚意与妥帖之下烟消云散了。”
崔老师这样一位民法大家的加盟,之于复建之初正是急需人才之际的清华法学,无疑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崔老师在清华法学院的岁月,一晃已经过去19年了。在这19年里,他始终以其沉心研究、醉心教学的付出与奋斗,为清华法学的发展壮大,为明理学子的成长成才,为法治中国的不断前进,做出着自己的贡献。
明理廿载,创业艰难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甚是。然而清华法学的复建之初,却切切实实经历了一段“纵有大师而无大楼”的艰难。复建之初,尚无如今的法学院大楼“明理楼”。“当时法学系(直到1999才成为法学院)就在清华中央主楼10层弄了两个屋子作为法学系系址所在地,里面也只有系领导在里面办公,教师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如果没有需要就不用去了。总而言之,当时物质待遇、办公条件几乎没有,特别艰苦。”
物质条件的匮乏尚在其次,更关键的是当时的师资条件也是严重不济。“我是第七位来学院任教的,当时的情况是好多课程咱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教师,因此只有在外面临时聘用,临时聘用显然不如清华本身的教工,人家说有事不来就不来了,所以教学工作面临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了。”
甚至于,彼时的法学院因面临着“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窘迫,“搬家”故而成为常态。谈到搬家,崔老师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忆中就搬过几次家,从中央主楼到三教搬过一次,从三教到明理楼又是一次。其中有次搬家我还记得院里专门开过一次动员大会,做了详细的部署,谁和谁一组,这个组负责什么等等工作都安排得很周详。”直到明理楼的落成,方意味着几多风雨的清华法学终于由系建院,创业艰难的法学院也终于有了家的归宿,老师们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而此时已然是1999年了。作为96年即到清华任教,同时也是清华法学复建之业的建设者和亲历者的崔老师,对清华法学复建20年来的所历经的艰难困苦,自是有着别样的感触和体悟。“或许正是历经了复建当中的艰辛与不易,才使得清华法学在短短20年的历程中能够‘穷而后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崔老师如是感概道。
然而法学院的复建和欣欣向荣,对于我们明理学子乃至于整个清华学子而言,又是何其有幸!百年清华,纵使几多沧桑仍割舍不断那“人文日新”的深重情怀,忘怀不了笃志建成一所真正综合性大学而非纯工科院校的高远之志。法学院的复建,可谓清华人文唱响“百年归去来兮”的一声号角,而这声激荡人心的号角,正是如崔老师这样的老师们用他们的辛勤汗水、艰苦奋斗所成就的。除了幸运,我们更应感恩与铭记,并在师长前辈们的奋进中继续笃定前行!
谈法学教育理念
崔老师认为,在法学教育中,首先需要树立的是“公平正义”的理念。“处理法律问题都离不开公平正义,这是不能背离的,应作为法律人根深蒂固且伴随终身的一个理念。”在法学教育中第二个被崔老师着重强调的,便是法律的思维方法。“现在这个时代一切知识都更新太快,或许学生在法学院学习之时还是有效的规则、原理,可能过几年就变成需要修正、甚至是需要抛弃的东西,所以这些知识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法律人应该是通过训练而形成相应的法律思维及方法,就好比喝了一碗剧烈无比的酒之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所以在法学院学习,法律思维及方法一定要学到,而法学院那么多的课程,也并不是每门课程都能让学生有效地形成这样一个法律思维。而是若干门课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而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抽象角度讲就是法哲学或法理学的训练,接下来具体角度而言就是学刑法、民法、商法、民生诉讼法等。举个反例,像草原法、森林法,这种孤立的课程即使上一万个小时,也难以让学生形成一种健全完备的法律思维能力。”
其中,崔老师着重地强调了民法的之于形成法律理念和塑造法律思维的巨大意义。“在这么多法学科目中,民法又处在一个很基础的地位,即使是宪法上很多理念也是通过抽取民法中的理念而形成。尤其是对生活具体的指导来讲,民法无疑显得更直接、务实和‘接地气’。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民法无疑是处在一个非常基础和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学生如果民法不学好,很难说塑造了良好的法律思维及方法。”
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
在清华法学院的学生的印象中,崔老师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他曾一度长期坐拥清华法学院“四大名捕”的头把交椅,由此可见一斑。当然现在的崔老师也认为虽然严格教学是对的,但毕竟“整天板着个脸骂学生也不合适”,因此渐渐地退出“名捕”的行列了。
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说崔建远老师是“桃李满天下”丝毫不为过。他以其专注严格、率先垂范,所培养的学生中出了相当多的人才。“学生们的成才,我自己觉得好象并不是说因为我对学生们多么特别的要求,因此我有时候想,或许是不是与我自身是怎么做的有些关系。因为我自认为对自己有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我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只是是一个普通人。由于我出身与成长在农村,经历过很多很艰苦的生活,觉得做什么事都要努力才会有收获,大的方面是为国家为社会,小的方面也是为让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能更理想,至于靠其他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也靠不上什么,只有通过更吃苦耐劳地努力了。所以我有几个优点,一个就是能吃苦、特别勤奋,再一个就是锲而不舍地思考,我虽然天分没这么高,但我会明天继续想,后天继续想,不停地想。我听我的一些学生,比如说北大法学院的王成教授,他们说,‘当我们看到你总在努力的学习工作,好象无形中就给我们压着,我们就觉得也应该如此。’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崔老师如此谦逊地娓娓道来,让我们钦佩动容,也让我们生动地感受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意义与真谛。的确,当你身边有个如此认真执着、锲而不舍的师长之时,你又有什么理由不以师为范、严格自身、不懈努力呢?
为师严厉 冀生成才
崔老师不仅“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对待学生的严厉,对待教学的认真,也是一以贯之的。现在各个高校都会开展由学生对老师进行“教师测评”的制度,而教师测评的结果,往往对老师的考核、评职称等“利益”密切相关。这就导致了一些老师忌惮学生对其进行“差评”而不敢过于严格地对待学生。
然而崔老师不仅不怕这个制度,而且为了让学生成才,纵然是面对各种风险与阻碍,也义无反顾,“我不怕学生给我打不好的分数,严格要求是为学生们好。因为很多学生是不具备由出身、家庭等外在因素所带来的优越条件的,比如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就算有的学生你有诸多优越的外在条件,也都只是暂时的,归根到底还要看人自身内在条件、靠本事不可。因此我在法学院课堂上,包括一些公开场合也会讲,学校教育应做大两点:一个要让学生做好人,第二让他学本事。学各种专业课程就是让学生长本事,如果学生们既是好人又有本事,走向社会难道他的工作会不优秀么,他优秀了旁人会不支持他吗?如果学生们的成长都遵循着这样一个轨迹,那么无论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容易逐步成才。但如果教给其他的这些投机取巧的办法,那么这样的‘成长’是不能持久甚至最终会误人子弟的!”
对于严格教学的这一问题,崔老师明显非常看重,他继续严肃认真地说道,“所以在民法的教学要求中,我就是这样严格要求学生的。这一期我上本科的《债法》,有的学生就很不适应。迟到了我会让他先别坐,先站着听一会儿;或者随时搞一个小试验来考核一下。所以我的邮件里经常接到各种解释理由,比如‘老师我今天脚崴了’诸如此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话,如果这个课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这样的话学生是成不了才的。尤其对于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智商天分都很高,我上课有体会,很多东西我一点学生们就明白。既然我们清华拥有天资这么优异的学生,又有这么好的师资条件,如果不更严格地要求学生,不更好地教育他们成才,那太可惜了!”
当然,崔老师也非常相信老师严格要求的做法,终归会获得学生们的理解和认同。“对一个上进且正直的学生来讲,当时你骂他一顿他可能觉得脸发烧、不高兴,但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老师这么严格要求我是对的,如果老师当时纵容了我,那我或许就放纵堕落了,最终本事学得不够,徒增未来的压力与困顿。”不知不觉间,崔老师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谈及这个问题,从他的述说中,我们能确乎感受到崔老师对学生们无比真切的关怀和对教学高度的重视。而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崔老师“为师以严厉,冀生以成才”的一片赤诚与苦心。
以学术研究奉献法治中国
崔建远老师作为当今中国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著述丰富且影响巨大,其诸多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民事立法以及司法实践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崔老师以其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崔老师认为,咱们国家正处在民事立法这个阶段,所以他的很多的研究就是为立法服务的。“比如我得了好几个奖的,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一部书叫《准物权研究》,这个书之所以能够催生出它来,就是基于立法的需要。因为当时要立《物权法》,那就涉及到比如说采矿权、养殖权等权利,是否应该由《物权法》规定呢?我当时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凭拍脑袋决定,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符合《物权法》的相应立法意旨、权利范畴等因素后才能最后做出决定。基于这些问题我就开始思考、写论文,一篇接着一篇,写着写着有的学生就说,你写了这么多关于这些权利的论文,那为什么不把它们体系化地整理出来形成一本书呢?我说这是个好主意,于是这样就有了这本书。现在民法学界的一个大事件是咱们国家进入到了《民法典》编纂的阶段。前几天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开会,说下周二要讨论的就是民法总则的体例——比如第一章写什么,立法需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所以我相当多的成果是立法‘逼’出来的,要回答这些由立法所提出的问题,就必须在学术上进行大量深入的思考。”
除了进行理论研究,崔老师也会接触较多的实务,而这些实务工作对崔老师的研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担任了十来个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我认为做研究也是需要了解实务的,比如民法刑法之类的法律,它们是解决实际生活中问题的法律,你不了解实际的话所做的研究也可能是抄来的,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在这些领域我们更进行需要‘接地气’的研究。了解实务为什么重要,举个例子来说,很多商人已经把立法时你想都想不到的合同形式,在实务中给设计出来了,我们也就只好跟着人家的实践来整理,再上升为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
崔老师坦言,正是对实务工作的接触和了解,为其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激励和灵感。“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在接受各级法院、各种律师事务所的邀请参与了很多实务案例讨论后,我会把这些材料带回来,有用的就存在电脑里。有时候这些材料及其思考就会形成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的章节。待时机成熟后,就把这些成果整理出来形成一个“文件夹”似的汇总。这些成果源自于实务提供的启发和思索,与此同时这些成果也恰恰是最受职业律师和法官欢迎的。他们在处理一些实务案例之时,往往就会直接查看这样的“文件夹“似的成果汇总,看能不能有类似案件的分析,一查找之后往往能够有所发现和借鉴。这就为实务工作者节省了许多精力,非常有助于实务的需要和便利。”
【记者手记】
千古名篇《师说》曾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崔建远其为师者,传以公平正义、拼搏奋进之正道,授以法学智识、法律思维之志业,解以学之疑窦、人生际遇之困惑。
其为学,亦孜孜以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名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求进之道,数十年如一日笃志前行,未曾一丝轻慢与怠惰。
无论为师抑或为学,崔老师始终以身立教、以德立身、率先垂范,不仅让我们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敬佩,也让我们由衷发出“景行行止”之热望。愿吾辈学子以师为范,效法恩师,接续并发扬清华明理人的精神与志向!
采访撰文:倪弋、楼淑颖(2013级法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