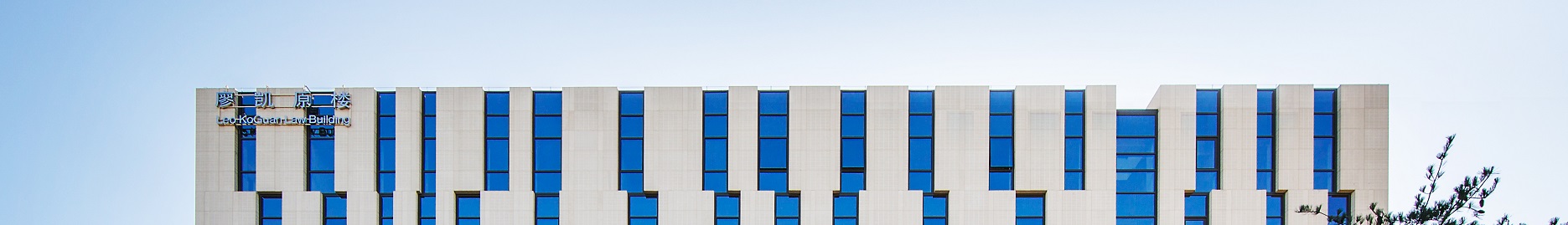易延友,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出版《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陪审团审判与对抗式诉讼》《沉默的自由》《冤狱是怎样炼成的》等专著十余部。发表《刑事强制措施的体系及完善》、《论最佳证据规则》等学术论文数十篇。座右铭: “心系自由律令,胸怀至上美德”
泥土中成长
易老师的故事是从他印象最深的小时候讲起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很偏远、很落后的乡村,地理位置在湖南西部,跟贵州接壤。“那里很多大山,真的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穷山恶水,但是山清水秀。我是从泥土中长大的。”
易老师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对他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多的期待,认为让他为在家里干活比上学更重要。所以易老师要边上学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当了很久的牧童,还要一边上山砍柴。稍微长大一点之后要参加春夏之交稻田的插秧和秋天的收割。秋天还要上山把之前种下的黄豆拔出来,担到家里晒干,然后用土制的工具把豆子砸出来,再把那些掉落的豆子捡起来。这些劳动有些很累,有些很无聊。我就是在这些劳动中长大的。”
易老师从小学5年级开始寄宿,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大约25里地,每个星期回家一趟。“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的食物都要自己准备,我会从家里拿着事先做好的酸豆角、酸菜、豆腐乳、南瓜藤之类的东西,这些食物可以放很久,然后自己挑着米,到学校过过秤,食堂就会给你发饭票。农民没有钱买米,只能带着自己种的粮食,一天到晚只吃自己带的菜。印象非常深的是,因为这些菜没有什么油水,我随时都是处于饥饿状态。这种状态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初中三年级。我一直觉得自己智商不够高就是跟那段时光营养不好有很大的关系。这中间也有几个老师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初中语文老师和高中的数学老师,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
高考,走出大山
随着年龄的增长,易老师渐渐觉得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时候农民做的活,就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没有任何知识含量,也没有任何挑战性。当你一天到晚不断地重复干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就觉得这一天很没有意义,生活没有希望。所以我很同情很理解某些流水线上重复工作的员工们的处境(他们的工作比起农民的劳动还是要轻松一些)。我对自己一辈子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很不甘心,所以到了初中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个很简单很朴素的想法,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那时的生存状况很苦,所以要发奋考出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世界、改变社会之类的大作为。我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就在多大程度上造福了社会。马云在创业之初也不见得就是要立志改变世界的,他可能也只是单纯地想改变自己而已。”
在上高中以前易老师的首选目标是上中专。因为那时考上中专意味着“农转非”,报考中专是那个时代农村子弟跃出农门的最好途径。易老师报考的是比较热门的商校。“不知是因为自己努力不够还是智商不够,反正差了几分没考上,最终去了高中。现在的农村商业合作社什么的都倒闭了,如果那时我去了商校,现在可能早就失业了。幸好当时没考上!当时农村中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孩子都去了中专,这其实是那个体制的悲哀。当然,如果他们不去读中专,重点大学估计也没我们的份了。有时候人的命运也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易老师的高中母校黔阳一中是一所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比清华大学的历史还长,1909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高中的生活差不多也是玩过来的。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在班上排第五名,但是最差的时候到过班上第20多名(一共50人)。大概到高三我才彻底进入努力拼搏的状态。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改革,不考数学,只考四门课程: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像政治、历史下功夫背就好了,而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我记得高三期中语文摸底考试,100分的题我考了91分,全年级(300人)第二名才79分,再往下就是50多分了,就这一门课,我的优势就出来了。我觉得自己语文好一个是靠兴趣,一个是靠积累,那个时候书不多,能逮到什么就看什么,感兴趣就背。我现在仍然保持每年至少要看10本以上的除法律以外的书籍的习惯。”
数学是令易老师头疼的一门课程。“它就像一把剑时刻悬在我的头上。高考时虽然不考,但在高三第一个学期期末,全省统考数学,如果不通过,不能参加高考。统考前有一次摸底考试我数学只考了56分,数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的训了一顿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语文再好,数学不及格,你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老师的话警醒了我,我发愤图强了好一阵,最终顺利通过统考。现在想想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到现在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在首都,迷惘中警醒
转眼讲到了易老师的大学生活。易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人生是由欲望和痛苦组成的,人一旦没有了欲望,从而也就没有了痛苦,最终也将陷入无聊。”他说自己的大学前几年就是这么无聊。
“一个农村的孩子,突然跑到首都这么大一个城市太不适应。在我们家乡,怀化就是大城市了,上高中以前我连怀化都没去过,上高中后也只是去过几次怀化,突然之间来到北京,找不到方向,也没有目标。这可能也跟我刚才讲的从小没有远大志向有关系,没有远大志向突然来到北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那时我想毕业后能够回到我们家乡的中级法院做个法官就心满意足了。所以那时候没什么追求。”
“大一大二我过得恍恍惚惚,导致对自己的评价显著降低,并且没有了信心。我到大三的时候决定好好努力下,就算只是为了奖学金也该好好努力下。那个时候我们的课程85分以上是优秀,如果你所有课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优秀的话,就可以拿一等奖学金。那一年10门课我有8门得了84分,我觉得太无奈了!每门课只差一分,老师们怎么就这么跟我过不去呢?后来想想,其实还是自己不够努力吧。”
“现在的大多数孩子大学也是混,有的人混的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有的人混的有所警醒。我想,我就是警醒的那一类。我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作了深刻反思,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明确自己将来想要干些什么,但我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考研,焕发朝气
易老师的研究生生活很充实。他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有个很好的去处——深圳海关。“我曾经想过如果当时去了深圳海关会是怎样!但是现在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依然选择做老师,做法律这一行!”
易老师考大学的时候,包括填志愿,一路下来都是法学院。“最开始也不是因为真的喜欢法学,而是因为法学专业可以帮我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个法律人。我想,自己可以去法院,法院去不了可以去检察院,检察院去不了可以去公安局,就是这种很朴素的想法。”
“对法学的兴趣和真正的喜欢是在上大学之后。大四的时候,为了考研继续攻读法律我埋头读书。之前玩疯了,心静不下来,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坐在教室里,哪怕什么都不看,也坐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月把心收回来。大四上学期的时候,我天天看书,上午7点看到12点,下午2点看到5点,晚上6点看到10点。我有一个详细的规划,上午看什么,下午看什么,看多少遍。看书的过程中有很多思考,既包括对人生的思考,也包括对学习内容的思考;我有时觉得那些书上说的都不对,将来如果我来写书,我不会这么写。”
“考研的过程是我重新焕发朝气的过程。人在奋斗的过程中一定是充满朝气的,一定精神是向上的,而一个人一旦奋斗完成后疲软下来,他处于空虚状态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就完了。考研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锤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对社会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这个过程让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求学不辍,受益终生
在后来的求学中,易老师又遇到了两位对自己很重要的老师,一位是硕士导师李宝岳教授,一位是博士导师陈光中教授。“前者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在学术界没有陈先生出名,但是却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关照有加,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
易老师在博士期间去了英国华威大学,国外的一年求学经历使他受益终生。
“出国前为了准备雅思考试,我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在新东方参加培训班,每周有两到四次的培训。北京的冬天晚上很冷,我经常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等公交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现在的付出值不值?现在证明这是值得的。后来我雅思考了6分(很惭愧啊),可以去英国了,现在你们至少要考7分吧。从国外回来后我就博士毕业了,推迟了大约半年的论文答辩时间。那个时候求职四处碰壁,哪都不要我,后来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收留了我,我在那里工作了半年。”
结缘清华,情有独钟
“读博士的时候就我觉得自己应该来清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一直没有刑诉的老师。”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14门主干课之一,一个没有刑事诉讼法教师的法学院是不完整的。易老师2003年1月份正式加入清华,成为这里第一个正式在编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师,从此以后清华法学院才完整了。
易老师能来到清华,一是有法学方面的学术造诣,二是有海外留学经验。他在上博士期间就出版了专著《沉默的自由》,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他在研究生阶段就在《比较法研究》上发表了论文;除了发表论文外,他还从研究生三年级起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很多篇随笔。凭着自己的努力,当时的易老师也算是小有名气。
“真正读了博士后,我就只想来清华大学了。”
易老师觉得清华特别适合做学问。“我的性格不是很外向,做学问只要勤奋努力,就不会辜负你。任何人,当你在社会去竞争资源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会用各种手段来打碎你的梦想、毁灭你的努力。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他毁灭不了的,那就是当你追求的目标是你自身的强大的话。做学问就是这样一种职业。你只要自己愿意付出努力,没有人可以打败你。你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你掌握一定的方法,你阅读大量的文献,然后你有所感悟,形成文字,自然会有刊物愿意发表你的东西。只要你有原创性,有自己的思想在里边,别人没看过的你看过,别人没想到的你想到了,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是很宽广的。做学问这个职业特点就是,你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张扬;想要取得多大成就,你就付出多大努力,不需要处理特别复杂的人际关系。你不需要考虑你的竞争对手有什么样的人格,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你只要跟你自己竞争即可。”
“清华的氛围特别好,大部分人都是在做学问,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个法学院不在于它有多少人,而在于有很多人在潜心地做一样东西。人多了不一定好,人多了以后什么人都有,可能会冲淡某些氛围。”易老师到清华时清华正式在编教师一共52人,他是第53个,倏忽之间已经将近12年了……
【记者手记】
本篇访谈纪实中,易老师主要谈及了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引人深省的人生体悟,让笔者深深感觉到老师于艰难困苦中的发奋图强,在人生困顿中的笃定前行,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然而在易老师身上,更为让我们钦佩与动容的,是其心中自始而终秉持和坚守的“公平正义”之信念,并为此信念亲身笃行鞠躬尽瘁的付出与践行。就如在社会当中引起热议的陈满案中,易老师便自发担任其重要申诉人。陈满一案在易老师接受代为申诉一年后,迎来了转机。曙光初现的背后,有着易老师除夕夜依旧撰写申诉状地认真负责,多次前往监狱了解案情的不辞艰辛……其间,易老师的法理论证逻辑缜密、证据调查详实充分,为该案的申诉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
对于法律人而言,确乎也没有什么价值是比“公平正义”更为高尚的了。易老师的努力与付出,既出于最原始的正义感与慈悲心,也源自于法律人对“公平正义”的笃定与坚守。在匡扶正义的路上,易老师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坚定不移地前进着……
采访撰文:马泽、武琳(2013级法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