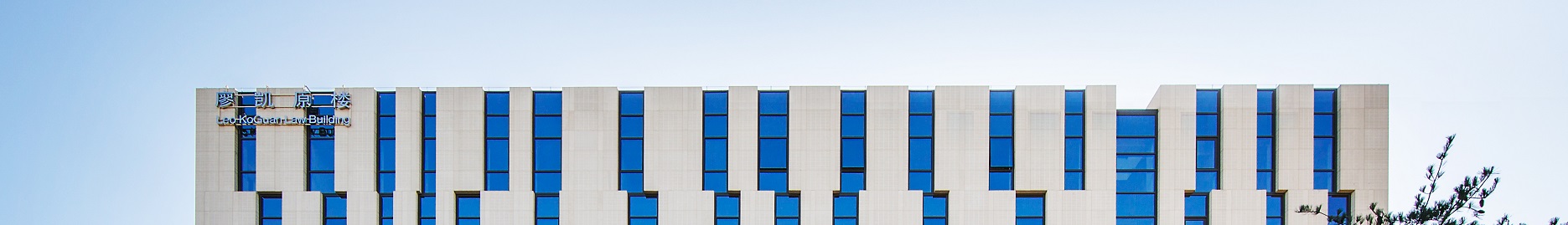申卫星,吉林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德国科隆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教学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总论、物权法、德国私法、卫生法学等。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记者:首先恭喜您被评为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在此之前荣膺这一称号的都是法学各个领域的翘楚,可以看出您对民法领域的卓越贡献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肯定。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谈,能够向您请教,也期待您能为法学院同学们就民法学习提出宝贵的建议。
申卫星教授(以下简称“申”):谢谢你们,实在过奖了!
要注重做读书笔记
记者:我们之前了解到您最初进入吉林大学是攻读理工科学位的(数学力学系)。那么,是什么让您选择放弃原来的专业而选择了法学领域?
申:其实最初,我对法律的认识也不是很完整,觉得学法学的人一来是会耍嘴皮子(受全国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二来就是会背而已。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学的英语角认识了一位学习国际法的同学。我听他介绍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才发现法学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于是带着好奇心,我开始阅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我看得非常入迷,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到最后几乎摘抄了全书80%-90%的内容。虽然摘抄特别辛苦,但是内心深处觉得孟德斯鸠写得太好了,不舍得不抄。经历了这个过程,我开始觉得法学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学科,因而产生了转系学习法学的想法。可以说是读书让我改变了对法学这个学科的看法,培养了学习法学的兴趣。而读书的过程中我特别想强调做读书笔记的作用。因为这个过程实际是在整理作者的写作思路,在构建一个完整的论证结构。做读书笔记的过程中又一定要用笔来写。用手写字,摘抄地越辛苦,你会和作者的心贴得越近,理解的不仅仅是作者的思想,还能体会到作者的感情。
而关于转系,其实当时吉林大学的政策还是比较严格的。成绩前三分之一的同学才有资格转系。而当时申请法学院的同学一共有12个,法学院方面只录取其中三人。不过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一个是因为我当时是班上的第一名,学习还是比较用功刻苦的;其次我也在转系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最终,我幸运地进入了吉大法学院。
如愿进入法律系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那个时候几乎是一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因为我和本来就是法学院的同学不一样,我是通过转系才争取到了这个学习机会,所以我一直格外珍惜。同时正如前面说的,我自己本身对法学学习也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总的来说,我学习投入的劲头特别足。每次上课我都坐在第一排,课堂认真听,下课和老师积极交流。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顺利的,后来就遇到了一些困惑。我感到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底子太薄,虽然逻辑很清楚,但是自己能够说的东西太少。我后来反思总结,还是因为读书太少,于是我又开始拼命读书努力涉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那个时候读书真的是因为对知识的那样一种渴望,目的非常纯粹,就是希望学习新知识。我们现在的孩子读书的时候可能想法比较多,但是我一直觉得学习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成长,为了那种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状态。我一直非常欣赏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觉得读书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的气质都被提升起来。大学的应有之义,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地学习、研究。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多读书,而且要勤于动手去做读书笔记。
学习有三个阶段:学懂、讲明白、写清楚
记者:我们之前了解到,您先后在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从事研究或者教学的工作,还包括在德国有过访问学者的经历,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这些从事教研工作中,您觉得哪一段或者那些经历是您获益最多?
申:其实没有所谓的“最多”,我求学的生活还是比较简单的。我1989年进入吉林大学,学习很刻苦,以勤补拙。后来1992年毕业开始做老师,一直到现在。1997年跟随我们院崔建远老师做研究生,后来又跟随江平老师读博士。期间我去德国科隆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2001年到2003年,我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跟随魏振瀛老师。可以说,每一段经历都是有非常宝贵的收获的。如果一定要讲一个“最”字,我觉得本科阶段其实作为我学习法学的一个“启蒙阶段”可能在学习习惯上对我的影响最大,而之后的学习经历则是在研究领域上不断深入的一个过程。
在吉林大学读完本科之后我就在吉大任教,读书加上工作一共十三年。十三年的时间的确使我对吉大有着深厚的感情。不过感情深厚不仅仅是因为时间久,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了研究的方向,打下了良好的法学底子。我记得刚刚开始教学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当时的年轻老师大多是研究生,而我本科才刚刚毕业,其实还是个学生。最开始讲课的时候,腿都发抖。后来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自己获得了很大的提升。我意识到清晰的语言和妥帖的例子对于教学的重要性。同时我开始逐渐明白自己弄懂和给别人讲清楚是学习的两个不同境界。现在我也经常和同学们强调学习有三个阶段:学懂、讲明白、写清楚。如果讲不明白,那本质上其实是没有真正学懂。写清楚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求我们以书面形式把自己的弄明白的东西严谨地、有逻辑地传递给他人。
后来在政法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恰好是《合同法》、《物权法》的起草讨论阶段。江平老师民商法起草小组组长,因而我有幸接触到了很多民商法立法理论和实践的信息,有时候甚至可以参与到相关的会议中去,真正地开阔了自己的事业。印象最深刻的是1999年《合同法》通过之后,我和另一位江平老师的博士生一起写作了一篇论文,《论新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这个机会叫我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特别深。之后的深造学习大抵都是如此,通过一些机会深入学习,对自己研究的东西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
考博士的时候,我听说了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的机会,我就报名去德国深造。当时其实一点德语都不会,后来被录取之后我就去北京语言大学学德语。从1998年9月到1999年7月,每天上半天课,下午复习。沉下心来学习了这一段时间,语言提高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学习,特别是语言学习,还是要沉得下心来去集中钻研,否则散兵游勇就收获不大。
后来我就去了德国做访问学者,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德国学者理论的精细和思维的严谨。比如,我们讨论的时候,老师会不断问,可以向谁,请求什么,请求权基础是什么。这种严谨思维台湾继受地很好,当然台湾现在也有“手册法学”的反思。但是大陆民法还是在严谨上要更下功夫。
学东西就要学准、学透
记者:您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凭借执着和努力,成为学术翘楚。其实同学们有的时候想要做研究,可是却没有方向,没有方法,非常困惑。因此特别期待能够得到您的建议。
申:对于本科生来说,没有既定方向很正常。其实本科阶段本来就不需要过早地设定方向,而是需要广泛地涉猎。多读书,多学习,不要考试前一通背,考完试就全部还给老师。这就要求大家带着兴趣而不是背着负担去学习,大家要在学习中有主动性。目前的学生没有形成一种独立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我经常听到同学讲:“这个我不会,因为没学过。”大家的大学更多时候是:老师把知识粘贴复制到学生脑子里,再在考试的时候由学生剪切复制到试卷上。注意是剪切,都留不到脑子里。大家只看考的内容,考完试就把知识全部还回来。(笑)但是,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是研究型能力。王泽鉴老师曾经说法律人应该有三种能力:法律知识能力、法律思维能力以及纠纷解决能力。我们的学生不愿意去背法条、记住基础概念,认为这些不够“高大上”。可是真正遇到“高大上”的问题,因为基础薄弱,我们却又解决不了。可以说我们的同学上述三种能力都是欠缺的。我觉得学东西就要学准、学透,就像扫雪,扫干净一块再扫下面一块,不断向前推。不要好高骛远,否则扫来扫去还是没有一块扫干净的地方。因此,我建议同学们第一是要有兴趣,第二是要肯吃苦。想一想我们在美国的竞争对手每一周读160页材料,而我们却天天趴在手机上。我们要有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记者:大家在学习中经常遇到的另一个困惑就是论文写作不得要领,也就是您说的“写不清楚”。您觉得就学术写作方面,我们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哪些共性的问题需要去检讨、改进?
申:其实大家写不出东西来,更多的原因不在于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没有东西可写。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环境权的。当时我是本科三年级。老师讲到环境权的时候说环境权是一种财产权,因为环境污染主要涉及的是损害赔偿问题。但是我模糊地有一种感觉,觉得环境权不仅仅是一种财产权。因为环境污染显然不仅仅带来财产损失,而且可以带来人的身心损害。因此我就去查了很多资料,去检验自己的想法,甚至还翻了百科全书。最后在当时一位老师(郑成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论文还是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你得有值得写的东西,然后再写。而对于写作无从下手,我觉得还是读书不够。要多阅读文献,积累相关知识。写作需要充分论证,横看成岭侧成峰,而不能形成盲人摸象的假象。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要在煎熬中去沉淀、积累,这个过程是自己成长所必须承受的,不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
基础和博雅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要去修正
记者:您在清华法学院已经有十一年了,通过您的教学经历,您如何评价当下清华法学生的学习状态?什么是值得肯定的?什么又是不足的地方?
申:我在清华接触到的学生很多,我觉得很多同学都很优秀。可是法学院老师们普遍的感觉是大家的学习氛围不浓,社会活动太多。现在有一个说法,大家都喜欢“水课”。这个我一直很着急。怎么能有水课呢?是教师的课上的水?还是同学们普遍学得水?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老师和同学们来反思。一方面老师是不是认真准备了,课程质量是不是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大家是不是认真对待了?现在好像能够出全勤都是一种“难得”,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清华的同学很优秀,从各地千挑万选选出来,来到法学院,我们老师都觉得责任重大。可是不可否认大家的学习状态也有很多问题,很多人甚至说“清华的孩子被宠坏了,好像给人感觉‘我没去北大就已经很给面子了’”。(笑)比如在评选讲评民商法奖学金的时候,政法大学几千人竞争十五个名额,清华二百人都不到就有三个名额。大家却不珍惜。去年面试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学连善意取得的基本概念和框架都不熟悉。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大家看不上知识能力,可是没有知识能力,又怎么来构建思维能力,乃至纠纷解决能力呢?夯实基础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要把自己的学习的东西建成一个完整的建筑,要知道每一个知识点在哪里,要有整体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谈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们的同学在“高大上”的领域里,事实上也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所以,我们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要去修正:一是增强法律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而是关注基础之上博雅的法律价值和法律精神。
而我觉得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家要提高对自己的要求。目前我们的同学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而且是随着年级的增长越来越松懈。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过班主任,当时期末考试后,班上一个同学的高中班主任打电话过来和我质疑:为什么这个孩子在高中一直是第一名,到了法学院就变成了第17名?当然这个老师的想法也值得商榷。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刚刚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有竞争意志的,可是后来就松懈了。有的同学刚来的时候考个二三十名觉得很伤心,可是大学慢慢消磨了他的意志,大四的学生好像考个二十来名就很高兴,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当然,成绩和排名不是唯一的指标,“我就是最后一名,但是读书多,读得深入。”也是很值得很肯定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同学并不去努力读书,精神状态在日趋低迷。说的更直接一点,那种人生的斗志和“狼性”没有了。年轻人要有朝气,要敢拼搏。
同时,大学生活也要学会规划,要坚决执行自己的规划。比如这一年就读一本书,触类旁通,把这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学清弄懂,也是很好的。大家普遍的焦躁情绪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划和坚定的执行力。目标要单一,不要什么都抓,结果什么都抓不着,最终只是停留在浮躁的情绪中。要单纯一点,快乐学习,读书完善自己的心灵,你会有满足感和收获感。要甘于平淡和枯燥,最终会发现生活的乐趣的。
明天无需设计,从今天的努力开始
记者:清华人在未来国家法制建设的领域必定会发挥重要作用,您觉得面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潮流,法律人特别是清华法律人应该又怎样的担当?
申:清华法学人要有担当,要有学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第一,不要好高骛远,为人要谦逊,要踏实。第二,不要怕难,要吃苦。要想到将来在政治局、在乡村、在律所、在国际舞台、在大学讲台上的,都是你的同龄人。法学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是社会科学,是通过社会权利义务的分配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门学科,社会科学人才要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不要总觉得离自己很远。这个国家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明天无需设计,从今天的努力开始。只要努力,就不负青春韶光。年轻时干了什么决定二十年后会干什么,为二十年后起航多做努力。
【记者手记】
在我对申老师进行采访之前,并未与他有过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但是私心里却总觉得他定是一个温文尔雅、幽默风趣之人。果然,在近两个小时面对面的采访(或者更可以叫做聊天)后,“坐实”了我的第六感:对于我们有赞美之意的开场白,他摆手笑言:“不要抬高我,我只是清华大学一名普通的教师。”相对于荣誉的淡然,令申老师兴奋的是,由他代理的钱钟书、杨绛夫妇私人信札拍卖案二审胜诉,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利用法律维护人的权利,促进社会的发展完善,这才是法学家孜孜以求、梦寐向往的终极目标”。
不仅如此,申老师骨子里还带着一股山东大汉的质朴和坚韧。在采访最后,我们好奇地询问申老师,是否后悔当初转系选择法学的决定,他摇着头说:“从来没有过。”他觉得曼德拉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入狱27年,而在于面对不可感知的未来,他依然乐观、充满信心的活下去。而申老师的导师江平老师亦是如此,遭遇了巨大的磨难之后,他仍然选择相信法治。而法治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需要一批有信仰的人来完成,申老师也是其中之一。除了自己奉献在法治这条路上,他还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走向讲台,也走向立法,一代接一代,推动中国法治进步。
在近2个小时的对谈中,申老师娓娓道来,自信中满含谦逊、感性时仍不失理智,就这样慢慢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传递着自己的信念,不强求结果,但从不曾放弃!
[1] 本文是2014年申卫星荣获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后,《法苑》报所做采访。
采访整理:柳林(2011级本科)、潘婷瑶(2013级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