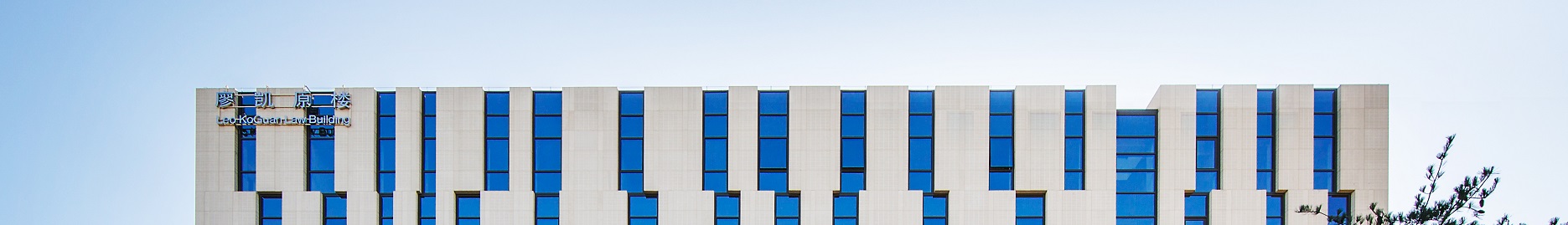林来梵,出生于福建福州。我国80年代末出国留学人员,曾赴日留学8年,先后就读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和立命馆大学,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学成后曾先后就职于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和浙江大学法学院,于2009年起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法学会宪法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林来梵教授是我国“规范宪法学”的代表性学者,曾出版《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宪法学讲义》、《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编)等代表性著作。
窗外繁盛的树枝随风摇曳,光影照进明理楼四层的一间办公室。见到我们,林来梵老师微微起身亲切地致意:“坐吧,椅子够不够?”于是,在这藏书甚丰的书房里,在周五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中,我们听林老师畅谈了他的人生,以及他对法学挥之不去的情愫。
“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
林老师将当初选择法学专业的原因总结为两个字:时代。他于1979年入读福建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对于法律的兴趣则来源于该系所开设的一门《法学概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政治、经济、文化均处于关键的转型期,万象更新,人心思治。林老师如此说道:“文革导致了人治体系的破产,动乱之后人人都期待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社会。我的专业选择正是受到了时代大潮的影响。”
虽说是大势所趋,但在当时选择以法律为业,渴望利用所学为国贡献的人却不多。20世纪80年代末,带着“治学为国”的时代责任,林老师踏上了赴日本留学的征程。留学日本八年可谓林老师法学学习的真正起点。在日本感受到的法治的强大力量深深地震撼了他,坚定了他学习法学的决心,“同样是受东方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由于走上了法治道路,日本就先于中国实现了高度的治理文明和经济发展。”
伴随着痛彻的领悟,彼时的林老师为法学的魅力如痴如醉,并最终选择了宪法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宪法与政治联系密切,是关乎治国理政和国泰民安的宏观思考。“在皇皇正论之中寄托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书生情怀,如政治般宏大,却不失法律的精美”,在林老师眼中,宪法学有着难以比拟的美丽。
在一切以实效说话,法律业务变身为金钱代名词的今天,宪法学却略显孤傲,他们注定不那么容易流连于实务界:理想主义,甘于寂寞,书生意气,这些原本用来形容诗人的词语放在宪法学者身上也丝毫不为过。林老师说,当今中国宪法学者也可以借用黑格尔曾经用来形容哲学家的那个说法来加以形容——“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法学在这个时代已是显学,是‘可为稻粱谋’的学问。宪法学虽在法学的绿原之上,但啃的却是枯草,宪法学者正有这种敢于为瑰美理想而奉献的精神。”
“让政治现实服膺于宪法规范”
1996年自日本归国后,林老师开始供职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此间,他出版了个人独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这本书是规范宪法学理论的础石之作。不久,书中所倡导的规范宪法学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国内众多青年宪法学者都开始自觉地运用这个宪法学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的宪政问题。
所谓规范宪法学,即从宪法的文本出发,重视宪法规范体系的自足性与稳定性,以达成宪法规范价值的功能。规范宪法学力图“让政治现实服膺于宪法规范”,让权力在宪法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其与当今党中央提倡的依法治国理念交相辉映。但曾几何时,这种学术立场也在法学界受到了“政治宪法学”等流派的挑战,对此,林老师认为,规范宪法学能够得以推行的关键在于“法学方法论的觉醒”——“从宪法文本出发,但不能被文本所禁锢。既要接受不能改变的,也要改变不能接受的。当文本与立宪主义相冲突之时,也要借机推动宪法规范的自我发展。”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悠久宪法传统,当代法治又未完全实现的国家,规范宪法学在中国的推广注定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漫长艰辛的过程中,以林老师为代表的宪法学者步步为营,他们丰硕的理论成果不仅在理论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响,也影响着立法与实务界。“中国尚未完成法治社会建设的历史课题,这也是规范宪法学面临的最大难题,但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依法治国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文人法学
2005年圣诞,林老师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法律博客“梵夫俗子”,这不仅成为了他与学生以及同行交流的平台,也是他激扬文字,抒发文学情怀的舞台。如今,博客的访问量超过260万,而博主却表示有些hold不住了:“搞得太热闹,访问量太大。”尽管如此,一旦聊起文学,林老师依旧有着掩饰不住的欣喜,“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中国正值文学兴旺的时期,当时好多人都可称得上是文艺青年。我也经常写写诗,组织诗社,现在也还偶尔写一些呢。我选择诗歌和选择宪法一样,都是非常理想化的行为。”
对于林老师而言,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它和法律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他曾提出过“文人法学”这一说法,并于2013年出版了一本同名书籍。这一概念的提出不单是他对于文学的深厚情感的体现,更是对一种由传统伦理向现代法治过渡的社会形态的描绘,而中国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正处于这个阶段。“文人法学是对正统法学的一种叛逆,它在一定程度上生发于当代中国部分法律学人对本国传统人文学问挥之不去的乡愁,为此也可能是如今我国从传统‘人文’到纯正‘法学’的过渡形态,它应和了法治启蒙的时代课题,寄托了法学家们的人文情怀。而这种人文情怀对滋养法学精神,推动中国法治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文学和法学虽是一个美丽的结合,但老师却不提倡学生们在法学写作中刻意加入过多文学因素。“纯正的法学和人文研究毕竟不同,人文法学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活动,没有深厚的功底可能会显得困难。但大学生却可从文学中学习精美的语言,学习中国传统伦理和家国情怀,这个没有年龄和阅历之限。”
谦谦君子,情系明理
浙江大学任教8年后,林老师于2009年加盟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优秀的师生群体,自由的学术氛围让老师颇感欣喜。他总结了清华法学院的两大特点,“一是国际化的雄心与视野,中国化的意识与归宿。我们有许多国外留学背景的老师,有丰富的学术会议,也开设了众多面向国际学生的课程,但却没有食洋不化,有着浓浓的本土情怀。二是看似人事纷繁,但自有内在的静好。学院没有给老师们量化的科研指标,每位老师都在自觉地以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做学问和教书,这是目前中国很多学院难以做到的。”
明理的学生们也给林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老师说,在清华学生身上能看到当今浮躁社会最缺少的安静和厚道。林老师希望学生们能够长久葆存踏实的作风,更希望有朝一日清华学子可重振君子之道,“君子彬彬有礼,不求私利,虽然有时很容易吃亏,但这个时代却很需要这样的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说的就是这回事儿。”
培养出有君子之风的学生,教育乃是关键。和法学院的很多老师一样,林老师注重学生的思辨精神和批判思维,但对他而言,“批判伦理和批判精神同等重要”,批判也应有君子风度。“东方的批判讲求‘慎思明辩’,即把道理说清楚,同时尊重对方的想法,对被批判者保持一种宽容与关怀。东方佛学中所言的‘水不洗水’一语,也折射了这一道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老师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每本教材的立论展开讨论,并进行深层的思考,同时他也会特别注意“充分尊重每种观点的存在”。
所谓“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如林老师所言,成为君子意味着不汲汲于眼前之利,转而承担起更为深远的家国之任。这“道”与“术”间的平衡对于个体而言是重要的人生命题,对于学院来说也是一个在思索中不断取舍的过程。作为国内一流的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在中国法治建设语境下承担了重要的使命,对于“我们该培养怎样的法律人才”这一常常被提及的问题,林老师认为,清华不但要培养掌握法律技术的“法匠”和高端的国际法人才,更要培养具有法律思维的各界领袖型人才。“在目前这一时期,哪怕是技术型人才、高端的国际法人才,仍然是人治大国中孤军奋战的一小部分人。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往往很容易被严酷的现实所征服,最后失去法律理想,自己也倍感痛苦。而我们现在需要培养的是志在各界,包括学术界、政界、商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当然也包括法律实务界等各行各业的法治人才,他们能够相互理解、密切配合、彼此支援,共同协力支撑起法治理想,以免其被现实所吞噬,从而促进中国法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这不仅是法学院的责任,更是每个明理人的责任。愿我们能不负林老师的期望,更能像林老师一样,偶尔从精致的法律条文中抬头,拾起一丝“文人情怀”、“君子之风”,于心怀家国的同时实现自己瑰美的人生。
【记者手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用在林来梵老师身上再贴切不过。林老师不仅积极鼓励学生们培养君子之风,自己更是君子之道的践行者。从当初毅然选择“绿原上啃食枯草”的宪法学,到成为规范宪法学的倡导者,再到兢兢业业地流连于课堂和书房,从林老师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位教师的厚德载物,更能看到一位宪法学者敢于担当时代重任的勇气。
采访结束后,林老师提出赠书。他担心书上落了灰,便反复擦了又擦,随后主动在首页题了字。此时此刻,很难想象面前这位高大宽厚的长辈是一位著名宪法学家,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者。想到海涅的一句话:“再高贵的灵魂也无权孤独,最高尚的灵魂最敏感于人间的寒暖”,心中之感动不免油然而生……
采访撰文:王心玥(2012级本科)、徐珂(2013级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