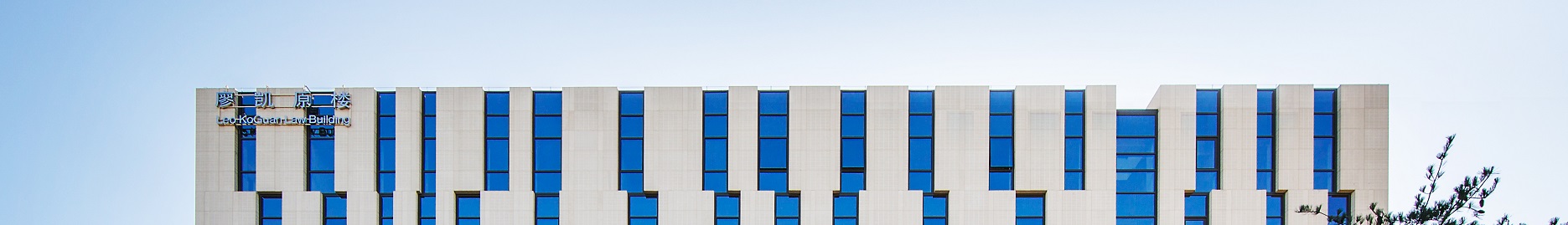文章来源:《法苑》第三十一期/2004年5月
法与生活:
编者按:法治的星空下,有一群这样的法律人,他们细细地耕耘着自己的那片田野,守望着想象的空间。在漫漫法路上,法律人留下自己跋涉的足迹,谱写着法路上点点心语。作为我等法路上之旅者,我们用法律来生活,用法律来思考,用法律来感知我等周身之万物。在那片想象的星空下,我等将法律的触角延伸及生活之诸领域,在看似作茧自缚的反复思辨中,释放心中理性的激情。
法典·诗篇
文/屠凯
以此土的经验,诗篇的出现应在法典之前。歌唱“刨土而食,掘井而饮”的长者,并不了解“帝力”与他有什么关系。享受日出日落的规律作息,尧是否拥有美丽的女儿,舜是否纵容乖戾的弟弟,都与老者没有什么相干。此土的法典,据说出自老者同时代的皋陶,火烧壁贮的历史记录了皋陶的讲演。皋陶对战俘施加刑罚,意味着一个神话时代的结束,尽管之后的千年中还有南方的智者反复赞美那个时代,但是历史的江河早已跃出那段冰原峡谷一往无前。然而,在皋陶的时代,似乎法典仍然是诗篇,既是政治举措,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文学型范。
保有上帝眷顾和大量知识的贵族继续皋陶的事业,制造着他们的秘密法典,周原殷墟上的健硕男人和曼丽女子则早已放声歌唱欢愉的情爱,灿灿桃英,漫漫安澜,养育出法典之外的诗篇。诸子开始讲学,诸侯开始征战,诗篇最富情感的郑地,产生了最早的公开法典,这是因为绚烂的感情需要规范么,还是那些热情女子更善激发士人雄辩的语言?邓析、子产的法典此土早已看不见了。能窥见端倪的只有李悝《法经》的残章断简流传。李悝生长的三晋,民风趋向质朴,正如今日的西北,黄沙之下只有粗旷单调的音乐驰骋在天地之间。《法经》经过商君卫鞅的整理传入了更加朴实的秦地,终于造就了此土第一个大一统大陆宇宙帝国。然而,雄壮的兵马涌似乎是不唱歌的,西北的狂风飘飏整个大陆,却只剩下东来的李斯在东海边写下几排小篆,诗篇被帝国法典命令燃烧作冲天火焰,从此,法典是法典。诗篇是诗篇。
唐是一个诗篇的时代。吴经熊把唐诗划分了四个季节,艳丽、奔放、沉重、凄楚,各美其美。唐也是一个法典的时代,《唐律》将统治未来的千年。然而,法典是法典,诗篇是诗篇。浸染突厥血统的唐廷臣僚字斟句酌的用门阀礼法注疏着旷世法典,继承士子精神的布衣书生却抛头颅洒热血写成讨逆檄文。法典更新注疏,诗篇变化风格,波澜壮阔的起义结束了,腥风血雨的叛乱平息了,摧枯拉朽的革命也终于过去了,唐亡了,留下几则此土后人流连忘返的故事,以及更重要的,一部缕析条分的法典和无数词采恣肆诗篇。
历史总是出现两次,一次悲剧,一次喜剧。薛允升将唐和明排比在一起,我却不知道哪一个是悲剧,哪一个是喜剧。以高尚而言,唐是悲剧,可末世的荒唐却是喜剧性的,以荒唐而言,明是喜剧性的,可甲申的壮烈却令人痛心疾首。明是一个无诗篇的时代,也是无法典的时代。如此漠视《明律》的新结构、《大诰》的大发行量,似乎只能证明知识的缺乏。然而,细致阅读《明律》的演化,却每每看到“大古里”、“哥哥行”似的北方气息一杀戮的气息、蒙昧的气息、猜忌的气息、贪婪的气息……如果法典离诗篇太遥远,难免显得丑陋粗鄙吧。“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此土女孩最鲜艳细腻的情致却面对“凡扮作杂剧戏文,不许”种种的限制,更有什么可说呢?
如果写一部法典能如写一部史诗一般,将会如何呢?一定有读者在此一笑,以为又是哪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展览一段痴心。也一定有读者在此一叹,以为法律教育的失败莫过于缺乏职业训练。其实段首的问题在过去的万年中早已被反复质问了无数次。爱诗篇的智者纷纷离开法律职业调头不顾,爱法典的匠人往往鄙薄辞章华彩直奔利害。可如果法典能像诗篇,更多的智慧可以在此土耕耘,更多的利害也可以赋予审美的色彩,不至使得诗人痛悼人文进化竟然还裹胁着肮脏的毛血,竟然还有有锋利的牙齿和未剪的指爪在撕扯社会,使得他们多写一章厌倦无奈的遗憾。法典是可以写成诗篇的。诗篇可宝贵的在于意象、语义、形式。如果此土的氓妇,可以分享若干对幸福的想象,可以使用同一种足够清晰优美的语言,可以欣赏带有某种特定节奏的文本,他/她们就一定可以拥有一部诗篇一般的法典。
我要一部诗篇一般的法典。